弘扬红色文化精神,创建红色文化产业,助力乡村振兴,铸就强国之魂。大家好,我是红色传承人郝文武。这里是南下支队红色传承第三百五十一讲,今天给大家讲的是,革命时期延安五老的故事。
延安五老,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,但是他们在革命时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,有这样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,他们被尊称为“延安五老”。他们分别是徐特立、吴玉章、谢觉哉、董必武和林伯渠。这五位老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,以其坚定的信仰、卓越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,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徐特立,生于1877年,是湖南长沙人。早在1927年,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,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为共产党人注入了巨大的士气。1934年,已近花甲之年的徐特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,成为红军中最年长的一员。长征途中,他克服了种种困难,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定的信念。新中国成立后,徐特立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,从不搞特殊化。他常说:“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相差太大,否则群众会有意见的。”他的这种精神,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吴玉章,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。他早年留学日本,加入了同盟会,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。在延安时期,他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,为边区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吴玉章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,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。
谢觉哉,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。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和教育家,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在延安时期,他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,为边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谢觉哉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法学功底,为党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董必武,生于1886年,湖北红安人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,也是新中国法制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。早在1921年,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,他多次身处险境,但从未动摇过坚持革命的意志和决心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、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,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林伯渠,湖南临澧人。他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,曾任中共七届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。在延安时期,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,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,建立三三制政权,实行精兵简政,开展大生产运动,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。林伯渠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无私的奉献精神,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誉。
“延安五老”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贡献,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们的事迹和精神,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在今天的和平年代,我们更应该铭记他们的功绩和精神,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。
延安五老也是窑洞里的不老传奇,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皱褶的深处。延安的窑洞里边,曾经摇曳着一盏盏的煤油灯。灯光下,5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伏案疾书。他们的身影被历史定格为。延安五老。因为他们平均的年逾半百,却以年轻人的热血在荒原上播种理想。这不是一个关于年龄的故事,而是一场精神力量的史诗。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,他们用知识、信念和人性之光为新中国浇筑了最坚硬的灵魂基石。
五老之一、董必武。
他是法治星火的守夜人。当国民党用枪炮围剿边区的时候,董必武在窑洞里用法律构筑了另一条战线。这位中共一大代表深知,革命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,更是文明的较量。他主持起草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,在战火中推行公开审判陪审制度,甚至允许被告请律师辩护。土匪也要辩护权,面对这个质疑,他掷地有声,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消灭人质吗?马锡五审判方式至今仍被法学界奉为圭臬,而这份对法治的坚守,恰恰是共产党人最超前的精神觉醒。五老之二、林伯渠。林伯渠是经济战线的红色掌柜,当时我边区的账簿上曾经写着触目惊心的数字,1941年,90%的财政靠外援。当国民党停发军饷的时候,58岁的林伯渠就戴着草帽走向了田野,他发明了三三制税收政策。让地主、农民共同来承担抗战的责任,组织军民开荒百万亩,硬是把饿死、解散、投降的威胁变成了南泥湾的稻浪。这位留学日本的财经专家用算盘完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它证明红色政权不仅能够打仗,更能够创造经济奇迹。
五老之三、徐特立,跪着讲课的教育圣徒。在日寇轰炸机的呼啸声中,43岁的毛泽东搀扶着67岁的徐特立躲避空袭。这一对师生,一个是革命领袖,一个是游击教授。徐特立创办的列宁小学遍布边区,课本是用树皮纸印的,黑板是门板刷的。他要求每个教师跪着也要把课讲完。
不是向命运下跪,而是俯身倾听贫苦孩子的心跳。当他把国际歌译成方言教给那些放羊娃时,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就在中国的农村扎下了根头。教育成了他最温柔的武器。
五老之四、谢觉哉,民主制度的泥土工程师。1941年延安的选举震惊了世界。不识字儿的农夫用豆子当选票脚夫在议会里边,哎,可以质疑干部的账目,这背后就是谢觉哉的一种土法民族。他设计的叫画圈法、烧动法,让80%的文盲实现了政治参与。面对农民不懂民主的嘲讽,他在解放日报曾发文说,你把豆子交给。
他们,他们比谁都清楚该投进哪个碗。这种扎根于泥土的智慧揭示了一个真理,真正的民主从来不是空中楼阁,而是生长在人民手心的温度里。吴玉章,跨世纪的文化摆渡者,从戊戌变法到文字改革,
五老之五、吴玉章。用他一生搭起了新旧中国的桥梁。当知识分子争论这个汉字存废,这个时候,他在延安就推广了拉丁化的新文字,却同时要求干部们要背诵说文解字儿。
看似矛盾的选择,却藏着更深远的考量,既要让陕北的婆姨能够写信给前线的丈夫,也要让中华文明的血脉不能断流。
他创办的延安大学走出了138位开国将军,而他临终前攥着的是未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草稿。一个老人用文化基因缝合了古今中国的裂痕,精神高原的永恒坐标。延安五老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1岁,这在战争年代近乎于一种奇迹,他们的长寿密码或许藏在那些不可思议的数据里。
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长时,平反了90%的冤假错案。林伯渠去世的时候,存款只有。两块银元。徐特立把大半工资换成了书籍,送给了灾区。而谢觉哉的一德书警句被刻在各级政府的门前,吴玉章弥留之际,仍在病床上批改着人大的教材。
这群老人们用行动重新定义了革命,它不是青春的专利,而是精神的远征。在生存与毁灭的悬崖边上,他们证明了一个政党最强大的战斗力不在于拥有多少枪炮,而在于能否让白发苍苍的智者依然相信未来,让满身伤疤的战士依然愿意为陌生人点灯。今天的中国已不再需要豆子投票树皮课本,但是,延安五老留下的精神地貌依然清晰,那是法治的敬畏、经济的尊严、教育的温度、民族的实感、文化的自觉,他们像五座烽火台,标记着精神的海拔。当物质的。高楼越建越高时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仰望这一片精神的高原。谢谢大家,今天就讲到,这里我们下期再见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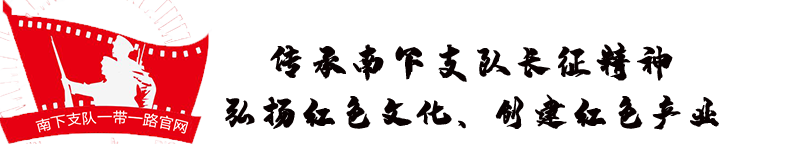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8780
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8780
 电话咨询
电话咨询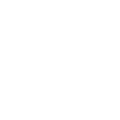 返回顶部
返回顶部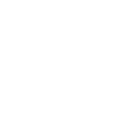 首页
首页